近读王持之先生的新著《酒诗漫说》,让我联想到了《葡萄酒概论》所言中国葡萄酿酒历史的悠久,原来先民早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就将葡萄与谷物混合酿造饮用了。
《葡萄酒概论》提到,2004年,中美科学家发表对中国贾湖遗址(距今9000―7000年)发掘出土的陶器内壁附着物的分析结果。发现“发酵饮料中水果的身份极有可能是葡萄”,并在遗址中“发现了野生葡萄种子”,由此得出“这是世界上用葡萄酿酒最早的考古证据”。遗憾的是,我国记载葡萄栽培及葡萄酒的历史已有3000多年,却多为一些传记类文字。
令我眼前一亮的是,王持之的《酒诗漫说》完全超越了那些传记类文字,他将读后感“青春的回想”“礼乐的和声”等连缀成了26说(章)。我从他的“清新与萧瑟”一说中惊喜地看到了葡萄酒的影子——南北朝时期,坊间传言“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的庾信(513年-581年),其40岁时(大约公元553年)所作的《燕歌行》中的诗句:“蒲桃一杯千日醉,无事九转学神仙。”王持之在书中坚定地写道:“葡萄酒入诗,一醉千日入诗,应该都是始于此。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称之为酒诗之绝唱了。”
谁料,王持之今天本想以漫说形式向读者贡献出他多年研究中国酒诗词的成果,却无意间为葡萄酒界奉献了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将之前人们以为的葡萄酒最早入诗的时间提前了近两个世纪。
我不免为集诗仙、酒仙于一身的李白感到遗憾,尽管他也写出了“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的诗句,写诗再多、再精彩却排不上葡萄酒入诗第一的名号,只能怪他出身于唐朝。而元代的耶律楚材,虽然也写了不少饮葡萄酒的诗,如“花开把榄芙渠淡,酒泛葡萄琥珀浓”“葡萄亲酿酒,杷榄看开花”等,但也只能被淹没在众多的酒诗之中了。
李白当不上葡萄酒入诗第一人,其实也怪不得他。在唐代之前,中国还没有开始自己酿造葡萄酒,基本上都仰赖于进口,直到喜好葡萄酒的唐太宗亲自出手,酒工在其监制之下,酿造出了八种颜色的葡萄酒,并将之御赐群臣饮用之后,“京师始识其味”。而庾信在品尝葡萄酒的事情上,可谓是占了天时地利。他当时是职兼文武的近臣,善外交辞令,自然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外国使者带到皇帝面前的琼浆玉液——葡萄酒。
庾信诗中的“蒲桃”,正好与史书《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载的今吐鲁番地区葡萄名称的写法多样,如“蒲陶”“蒲桃”“浮桃”“蒲桃”等吻合。尽管后来人们早已经习惯了“葡萄酒”名称的用法,但“蒲桃”这种写法,连周作人也在沿用,比如他的《谈酒》:“医生叫我喝酒以代药饵,定量是勃阑地每回二十格阑姆,蒲桃酒与老酒等倍之。”
提起葡萄酒,无人不知唐代边塞诗人王翰那首《凉州词》中脍炙人口的诗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然而,当你阅读了王持之的《酒诗漫说》后,再和友人品饮葡萄酒,别人又老套地引用王翰诗句时,你却悠然地将庾信的“蒲桃一杯千日醉”诵读出来,并且告诉对方此诗比“葡萄美酒夜光杯”还早近200年。好家伙,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如果你再把后面的诗句完整地吟诵出来:“无事九转学神仙。定取金丹作几服,能令华表得千年。”此时的你,早已不是诗人胜似诗人了。
从葡萄酒回到酒诗,在古往今来的各类饮品中,酒跟诗的联系最紧密。从先秦诗人低沉的“我姑酌彼金罍”,到汉代诗人高调的“斗酒相娱乐”;从唐诗中豪放的“与尔同销万古愁”,到宋词里婉约的“东篱把酒黄昏后”——酒不断激发着诗人的灵感,催生出不胜枚举的酒诗名作。打开王持之的《酒诗漫说》,便会开启一场芳气袭人的诗词之旅,读懂古人的诗酒情怀,体会中华文化的醇厚滋味。也许这正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唱响的一曲科技与文化相融合的壮丽情歌。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副编审、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农业科普创作专业委员会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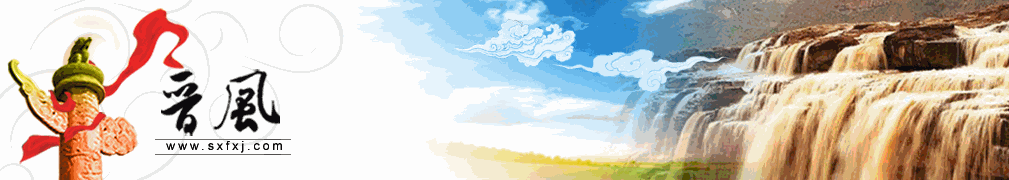



 来 源:
来 源: 时 间:2024-03-29 08:57:15
时 间:2024-03-29 08:5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