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膜拜团体与“新宗教”的界定主要有世俗反膜拜组织和宗教社会学两种进路。世俗反膜拜组织的代表国际膜拜团体研究会总结出膜拜团体的15条特征,由于意识形态的倾向和难以进行表征而被质疑。宗教社会学家将膜拜团体理解为实验性社会运动,并提出“看不见的秩序”这一概念工具,对于特定叙事、宗教神话和信仰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由于其外延过于宽泛,容易让人将膜拜团体与普通宗教等同起来,而忽视其危害性。宗教社会学的界定偏重理论层面,世俗反膜拜组织的界定更具实践性,面对中国膜拜团体治理的复杂内外环境,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应注意调和运用两种进路。
【关 键 词】膜拜团体与“新宗教” 界定 世俗反膜拜组织 宗教社会学 “看不见的秩序”
【作者简介】邵鹏,中共天津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四、宗教社会学的一种解决方案——“看不见的秩序”
1.“看不见的秩序”的定义
学者们已经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来界定晚期现代性社会中的“新宗教”,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概念叫做“看不见的秩序”(unseen order)。这一概念源于1902年,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爱丁堡大学著名的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中,将“宗教生活”定义为“相信有一种“看不见的秩序”,为这种秩序和谐地调整自己以达到至善(supreme good)”。
这个定义有三个主要原则:第一,它并没有把“宗教”限制在那些相信某种至高无上存在的传统之中,而是允许对宗教信仰与实践进行广义的理解。第二,这种扩大了的理解搁置了“真实性”问题,这个问题在围绕“新宗教运动”的文化语境中让利益相关方十分担忧。现在确定其是否为“真实”的问题已经不是关注的重点了。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它避免了所谓善良的、道德的谬论,即宗教在社会中总是代表善的力量、而负面的社会影响则源于错误或虚假的宗教实践。例如,阿兹台克人的“看不见的秩序”——假定战神的存在,战神永远在和其他神祗战斗,以保佑人民的兴旺。由于战神需要源源不断的血液来保持其战斗力,因此阿兹台克人有献祭活人的习俗。尽管这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但在阿兹台克人看来,这是为了向着他们所理解的“看不见的秩序”进行的“和谐地调整”。
2.“新宗教”有关“看不见的秩序”的实践
在很多情形中,“新宗教”的叙事不仅站在了广大社会的合法信仰的对立面上,也站在了调节人类关系的主流社会习俗的对立面上。例如,尽管“统一教”承认《圣经》的真实性,但该团体还是通过主张类似“文鲜明(Sun Myung Moon)受神启获得的关于这个世界的隐含真理,非‘统一教’成员无法获得”等特殊的教义,对传统基督教信仰构成了挑战。在“上帝之子”(现更名为“国际家庭”)的理论体系中,当下所有的基督教会都不具备正当性,因为他们都曾抛弃上帝,接受物质、堕落的以及邪恶的诱惑。“雷尔教派”认为,传统基督教对于《圣经》中创世神话的表述是一种误读。人类不是由上帝、而是由叫做埃洛希姆(Elohim,他们译为“来自天上”的先进的外星种族)所创造。这些埃洛希姆具有从DNA中创造生命的能力,并将地球作为实验室。类似的对立还表现在,许多“新宗教”都特别强调,人类已经同其最初目的相分离,从而导致了所有的罪恶、堕落与痛苦。例如“统一教”教义的一个突出主题,便是人类故意违背上帝的规划,带来了道德的沦丧以及归属感的缺失。其他群体,例如“科学教派”确信人类已经同他们自己身上的那种上帝质量失去了联系、同内在神性相割裂,陷入物质世界的泥淖之中。
每一种关于“看不见的秩序”的想象,都在实践层面上展示了他们对于“至善”的理解。就像“新宗教”的神话一样,他们的仪式与实践也具有对抗性质。“科学教派”的信徒认为,审察实践(practice of auditing)能够帮助他们克服随年龄的增长、以及由创伤所导致的身体虚弱。“统一教”教徒将文鲜明与韩鹤子(Hak Ja Han)夫妇当作“真父母”,承认文鲜明是基督复临,从而将“统一教”与上帝创造人的规划结合在一起。“上帝之子”的成员相信,通过重新阐释基督教长期以来对于人类性行为的立场,可以更加接近耶稣“将爱作为所有人际关系基础”的训诫。对于高级超验冥想修行者来说,“超验静坐”(TM-Sidhi)和“瑜伽飞行”(yogic flying)能够使他们所身处的物质世界和自然法则的“看不见的秩序”达到平衡。
3.将“新宗教运动”视为社会实验
在许多传统中,宗教共同体都是根据神话叙事体系与仪式体系组织起来。通过具体的组织手段,他们通过自适应以符合“看不见的秩序”的要求。“新宗教”在社交方面也不同于既有的宗教组织。尽管“新宗教”很难称得上“新”,但它们总是能够对一些古老的信仰、实践、仪式进行再发现、再融合和再创造,具有与众不同的社会特征。“新宗教运动”“新”在组织层面,例如大多数第一代会员,为推动相关运动的开展贡献了主要力量。通常来说,这些皈依“新宗教”的人并不能代表社会中的普通大众。“新宗教运动”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一些共同点:白人、中产阶级、受教育程度良好的成年人。这些运动常常被克里斯玛式(charismatic)人物领导,他们的思想构成了对既有社会秩序的挑战,他们的克里斯玛式权威为运动凝聚了力量。由于“新宗教”没有相对固化的组织传统,它们在组织形式上经常发生快速和频繁的改变,来适应其“生命”周期中的各种压力和挑战。
从这个角度看,可以把“新宗教运动”可以看作一些实验,通过这些实验,可以为一个新的、或改良后的“看不见的秩序”构筑共识基础,并且说服一些人加入它们,向着某种特殊的宗教观进行“和谐地调整”。就像在自然科学中一样,有些新的宗教实验会取得成功,见证一些学者所谓的新世界信仰的出现,例如,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摩门教)”视为正在兴起的世界性宗教。有些运动则在早期就失败了。还有一些宗教创新的实验对参与者和无辜的旁观者都产生了可怕的后果,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是1995年“奥姆真理教”对东京地铁的沙林毒气攻击。仅仅因为某件事是实验性的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本身就是高尚或明智的。比如“奥姆真理教”这类组织,为了追求他们对“看不见的秩序”的特殊愿景,做出了可怕的事情。通常,当“新宗教”开始运用“看不见的秩序”的相关观念时,争论也会随之而来,它们的实验对现有的社会秩序构成了挑战。有时,“新宗教”作为主流信仰的对立面,尽管规模小、力量分散,但仍然会与同现有社会秩序发生冲突,危及到主流社会体制。
无论它的视角是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艺术的或宗教的,当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对世界的理解彻底重组,在“新宗教”的情况下是对与世界相关的“看不见的秩序”的认识出现了根本性的重组,这就增加了与主流观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新视角不仅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思维方式,它还暗示主流的理解是不正确的。从广义上讲,宗教的本质是主张唯一的真理,而在宗教多元化的社会中,往往会容忍这些相互竞争的主张。然而,对真理的新理解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主流思想。这些冲突不一定是新认识或新行为本身的问题,而是根深蒂固的世界观和那些质疑其正确性的世界观之间的对立关系。宗教社会学家试图在复杂的背景下理解“新宗教运动”,他们试图证明无论一个团体是否被接受为合法的宗教,它都是社会、文化、政治的复杂产物,将“新宗教运动”与一系列固有宗教的特征进行经验地客观地简要比较是不妥当的。他们认为,最有用的方法是把那些被称为膜拜团体的有争议的群体理解为实验性社会运动。
五、对“看不见的秩序”的评论
1.“看不见的秩序”的优势
宗教社会学家提出的“看不见的秩序”这一概念工具对于分析膜拜团体和“新宗教”来说具有一定优势:第一,它可以激发对于特定叙事、宗教神话和信仰的说明,从而能够描述“看不见的秩序”的性质、阐释“看不见的秩序”同日常世界的关系,并说明如何使个体寻找到走向至善的道路。第二,这些神话故事在具象层面体现为各种规定性的行为、宗教仪式与实践。这些实践和行为用一种明显的、有意义的,以及对于实践者来说不可否认的方式,将信徒同“看不见的秩序”相联结。“新宗教运动”在文化意义上明确强调神话、信仰、仪式以及实践,这区别于既有宗教群体,也构成了它们与主流文化的显著差异。
2.“看不见的秩序”的缺陷
“看不见的秩序”只注意到“新宗教”的特别之处,以将其视为实验性信仰的方式,为其离奇的世界观和行为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但是,它却忽略了“新宗教”当中潜在或已经显现出的危险。尽管相关学者认为“天堂之门”的自杀事件、“大卫支派”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对抗等恶性事件只是少数,绝大部分“新宗教运动”都极为低调且安全,但是危害性的问题确实存在,且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加之媒体具有负面色彩的报道,使得人们对于“新宗教”的印象就定格于恐怖、奇怪、压抑与挑衅。若试图扭转人们对“新宗教运动”的固有看法,就应该更加重视其中危险的部分,仅仅将其看作“和谐地调整”并不能消除人们的恐惧。
“新宗教运动”与传统宗教在信仰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看不见的秩序”似乎认为任何宗教都有成为膜拜团体的潜在可能,只不过它们和谐地调整方式不同。而且普通宗教和膜拜团体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在实践上加大了辨别膜拜团体的难度。这种视角还会造成两方面的隐患,要么将所有合法宗教推向对立面,使人们谈宗教色变;要么将膜拜团体拉向合法化,宗教治理的成本将进一步增加。这其中任何一种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以上问题都出自一个根源性问题,即“看不见的秩序”外延过于庞大,它不但对膜拜团体具有解释力,而且似乎对所有宗教都具有解释力。由于这种宽泛的外延,使得人们容易将膜拜团体与普通宗教等同起来,从而忽视其危害性。尽管提出“看不见的秩序”的宗教社会学家一再强调这是本着客观的态度对膜拜团体进行学术研究,但是如果他们批判ICSA的苛刻是一种主观,那么他们的相对宽容是不是也落入了另一种形式的主观呢。
六、结语
膜拜团体与“新宗教”的界定始终是膜拜团体研究的首要问题和关注焦点,是对其警示、治理、帮辅等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世俗反膜拜组织和宗教社会学界对于膜拜团体与“新宗教”界定的争论主要体现在学术上。学界目前或许很难对膜拜团体与“新宗教”下一个各方满意的定义,但这并不表明不能对其进行研究。以ICAS为首的世俗反膜拜组织更关注膜拜团体与“新宗教”对人的伤害,为了揭露其危害在界定过程中多以操作性定义为主。但是很多负面特征并非膜拜团体和“新宗教”所独有,而这些定义在意识形态上就已经将其推向了负面。宗教社会学为了规避这个问题,没有急于对膜拜团体与“新宗教”下定义,而是利用“看不见的秩序”试图解释膜拜团体与“新宗教”的行为,但由于其外延的宽泛性,使得膜拜团体与“新宗教”和普通宗教的界限变得模糊。虽然二者存在各自的问题,但是在其自身的领域内无疑是成功的,ICAS的理论和方法挽救了很多遭受膜拜团体与“新宗教”伤害的人,“看不见的秩序”是被宗教学界接受的概念工具。二者的争论也不断推进着对膜拜团体与“新宗教”的研究工作。
在实践层面,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膜拜团体治理面临复杂的内外环境,国际方面,膜拜团体与民族、人权等问题相互交织牵扯;国内方面,新有神论、伪科学团体不断整合翻新,而且新型的膜拜团体的隐蔽性更强,不易甄别,如果与境外反华势力勾结将危及国家安全。这些新问题使得膜拜团体的治理工作增加了难度。ICSA的标准虽然在逻辑上不够完美,但是可操作性更强,对我们认识新形式的宗教提供了参考,尤其对一些膜拜团体在萌芽期就能有所警觉。至于“看不见的秩序”,可能在界定某个组织是否属于膜拜团体这个问题上并不能提供明确的判断指标,但是可以通过这个视角去深入了解和研究这个组织,为构建膜拜团体治理的话语和叙事体系提供一定依据。
1.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天津基层党建引领农村宗教治理模式研究”(TJKS21-020)阶段性成果。
2. Dawson, L. Comprehending Cults: The Sociology of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Second Editio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79.
3. Singer, M.Preface. //Langone, M. Recovery from Cults: Help for Victims of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Abuse,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3, pp. xvi-xix.
4. 陈天嘉、任定成:《从2012 年ICSA 年会看膜拜团体研究的新动向》,《文化研究》2012 年第15期。
5.陈天嘉:《复杂化与胶着态的邪教与反邪教运动——从国际膜拜团体研究会年会审视国际邪教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6. Singer, M. Cults in our midst: The continuing fight against their hidden menace (Revised Edi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3, pp. 7-10.
7. Langone, M.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Cultic Groups-Revised. https://www.icsahome.com/articles/characteristics. 2021-10-30.
8.Hunt, D. In Defense of the Faith: Biblical Answers to Challenging Questions. Eugene: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1996, p. 68.
9.James, W.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A Study in Human Nature.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94, p. 61.
10.Cowan, D and Bromley, D. Cults and New Religions: A Brief History (Second Edition). 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 2008, p. 8.
11.Bromley, D. Perspective: Whither New Religions Studies: Defining and Shaping a New Area of Study. Nova Religio, 2004, 8 (2): 83-97.
12.Stark, R. The Rise of a New World Faith. 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 1984, 26 (1): 18-27.
13.Cowan, D and Bromley, D. Cults and New Religions: A Brief History (Second Edition). 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 2008, p. 201.
14.Beckford, J. The Media and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 Lewis, J. From the Ashes: Making Sense of Waco.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4, p. 143.
15.陈天嘉、王贝特:《世界变局中的邪教治理:机遇与挑战》,《科学与无神论》2021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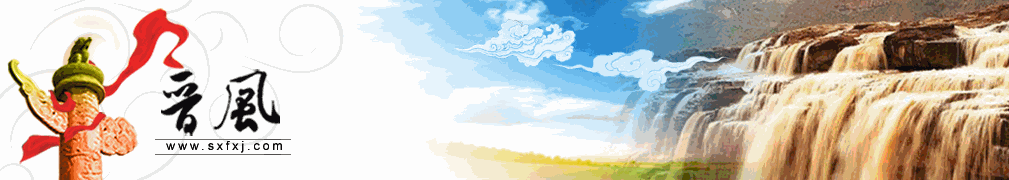



 来 源:
来 源: 时 间:2024-02-26 17:27:52
时 间:2024-02-26 17:27:52
















